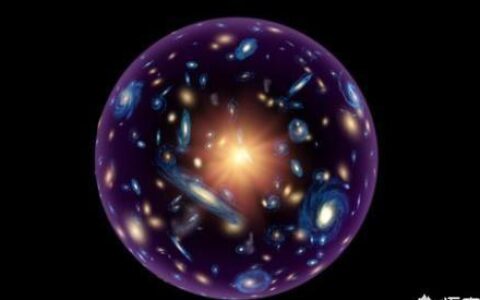旧相机的镜头蒙着层薄灰,我用麂皮布轻轻擦拭时,指腹忽然触到调焦环上深浅不一的纹路。那是爷爷生前反复摩挲留下的痕迹,像把岁月里的某个瞬间,牢牢刻进了金属的肌理里。曾经总觉得 “物距” 是物理课本上冰冷的术语,直到多年后整理旧物,才在那些定格的画面里,读懂两个字背后藏着的万千心绪。
第一次对物距有模糊认知,是十岁那年的春节。爷爷端着他那台黑色单反相机,要给我拍一张站在梅花树下的照片。他蹲在雪地里,反复前后移动脚步,冻得发红的手指一次次转动镜头。“再往后退半步,” 他声音里带着笑意,“这样花瓣能刚好落在你肩膀旁边,不远不近才好看。” 我那时只顾着数枝头的花苞,没听懂 “不远不近” 里的讲究,直到后来在相册里看见那张照片 —— 我穿着红色棉袄站在画面中央,一枝梅花斜斜掠过肩头,花瓣与衣角的距离,刚好能容下一缕冬日的阳光。
后来学了物理课,才知道爷爷当年调整的就是物距。课本上说,物距是物体到透镜光心的距离,这个距离的变化,会让成像出现虚实、大小的差异。可我总觉得课本里的解释太生硬,就像把爷爷相机里的梅花,摘下来泡进了冰冷的试剂瓶。真正的物距,应该藏在他蹲在雪地里的温度里,藏在我转身时花瓣落在肩头的弧度里,藏在按下快门那刻,他眼角眉梢的笑意里。
高中时住在学校,每个周末回家,都能看见奶奶在阳台摆弄她的月季花。她总说要给花拍张好看的照片,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角度。有次我拿着手机帮她拍,她站在花旁,反复叮嘱:“离花远点,再远点,要把整个花盆都拍进去。” 我不解地问:“拍花不应该靠近点吗?这样才能看清花瓣啊。” 奶奶笑着摇头,手指轻轻碰了碰花瓣:“你爷爷以前拍花,总喜欢把花盆也拍进去,他说花和盆是一起的,少了哪个都不完整。” 我顺着她的意思调整距离,镜头里,月季的枝叶舒展,花盆上的裂纹清晰可见,背景里还能看见阳台晾着的蓝白格子床单。后来这张照片被奶奶洗出来,贴在她床头的相框里,旁边是爷爷年轻时拍的、同样带着花盆的月季花照片。
去年整理爷爷的遗物,在他的相机包里发现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。翻开第一页,是他用钢笔写的字迹,歪歪扭扭却很认真:“给囡囡拍梅花,物距 1.2 米,光圈 f/5.6,这样花瓣不模糊,人也清楚。” 后面几页,记满了各种拍摄参数,有的标注着 “囡囡生日”,有的写着 “老伴浇花”,还有一页画着简单的草图,是阳台的布局,旁边写着 “拍月季时,镜头要对着东边,下午三点的阳光最好”。原来那些年他看似随意的调整,都是悄悄记在心里的牵挂。他从来没说过 “我爱你”,却把对家人的心意,都藏在了物距的数字里,藏在了每一张照片的光影里。
去年冬天,我带着爷爷的相机回到老房子。院子里的梅花又开了,和我十岁那年一样,枝头缀满花苞,在寒风里透着淡淡的香。我学着爷爷当年的样子,蹲在雪地里,慢慢转动调焦环。镜头里,梅花的枝干清晰起来,花瓣上的雪粒晶莹剔透。我试着调整物距,近一点,能看见花瓣上细细的纹路,却看不见整棵树的姿态;远一点,能拍下树的全貌,花瓣却变得模糊。忽然明白,爷爷当年说的 “不远不近”,不只是拍照的技巧,更是人生的智慧。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太近了会彼此伤害,太远了会渐渐疏远,只有找到合适的距离,才能留住最美好的模样。
我按下快门,“咔嚓” 一声,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。仿佛又听见爷爷的声音,带着笑意说:“再往后退半步,这样刚好。” 起身时,一片梅花瓣落在我的手背上,冰凉的触感里,却透着一丝温暖。抬头望向天空,雪花轻轻飘落,落在相机镜头上,融化成一滴小小的水珠。透过水珠看梅花,花瓣变得朦胧而温柔,像隔着一层时光的纱。
或许物距从来都不是冰冷的物理概念,它是爷爷蹲在雪地里的温度,是奶奶牵挂花盆的心意,是我们在时光里,为了留住美好而小心翼翼调整的距离。就像那台旧相机,镜头里装着的不只是风景,还有我们舍不得忘记的人,和那些藏在光影里的、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下次再拍梅花时,我还要调整物距,不是为了拍出完美的照片,而是想借着这个小小的动作,再和爷爷说说话,再看看他当年眼中的风景。不知道他在另一个世界,会不会也在调整着镜头,看着我站在梅花树下的模样?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
转载请注明出处:物距里的时光褶皱 https://www.w10.cn/suitan/7538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