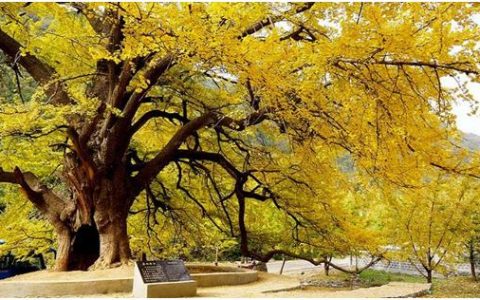祖父的座钟总在午后三点格外响亮。阳光斜斜切过八仙桌的木纹,铜制钟摆晃出细碎金芒,像把看不见的刀,在青砖墙上刻下深浅不一的划痕。我趴在冰凉的桌沿数钟摆,数到第七下时,祖父总会从竹椅上直起身,往铜壶里添第三遍热水。
那年我八岁,座钟底盘的漆皮已经起了卷。祖父用浸过茶油的棉布擦拭钟面,指腹蹭过罗马数字 IV 时,总会停顿片刻。“这钟比你爹岁数大。” 他说话时喉结动得很慢,像座钟里卡住的齿轮,“民国二十六年从苏州城带回来的,那会儿你奶奶还梳着辫子。”

祖母的辫子后来盘成了髻,再后来就躺在了后山的松树林里。我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,穿月白布衫站在座钟旁,两只手拘谨地绞着衣角。祖父说那天特意把钟调快了半小时,好让拍照先生赶上最后一班渡船。照片里的座钟指针确实歪着,像只被冻僵的蝉。
父亲第一次顶撞祖父,也是因为这座钟。十七岁的少年摔门时震落了钟顶的铜雀,零件滚到条案底下,发出细碎的哀鸣。“都什么年代了还守着这破烂!” 他吼声响得让座钟都停了摆,后来才知道是震松了机芯里的游丝。祖父蹲在地上摸零件,摸到半夜忽然说:“你娘当年就爱听这钟响。”
我十五岁那年,座钟开始走得忽快忽慢。有次半夜醒来,听见楼下传来咔嗒咔嗒的声响,像是有人在跟时间较劲。趴在楼梯扶手上往下看,月光正落在祖父佝偻的背上,他手里捏着副老花镜,镜片反射着钟摆摇晃的银光。“游丝松了。” 他头也不回地说,指尖在黄铜齿轮上轻轻拨弄,“就像人老了,骨头缝里总爱进风。”
那年冬天来得早,祖父在扫雪时摔断了腿。躺在病床上的日子,他总念叨着座钟该上弦了。父亲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钟上弦,可那钟像是认人,父亲上的弦总撑不过半夜。有天凌晨,我听见座钟又停了,下楼时看见父亲正对着钟摆发呆,他手里攥着块抹布,布角在钟面上蹭出淡淡的灰痕。“你爷爷说这钟有灵性。” 他声音很哑,像是从生锈的铁管里挤出来的,“其实是他自己舍不得。”
祖父出院那天,阳光把整个院子都晒得暖洋洋的。他拄着拐杖挪到座钟前,手指刚碰到钟摆,那钟忽然自己滴答响了起来。指针慢悠悠地转着,像是在追赶错过的时光。祖父笑了,眼角的皱纹挤成两朵晒干的菊花:“你看,它在等我呢。”
我考上大学那年,家里添置了电子钟。数字跳动时发出细微的蜂鸣,跟座钟的滴答声比起来,像是蚊子在哼。祖父依旧每天给座钟上弦,上弦时总要把电子钟的电源拔掉。“吵得慌。” 他说,耳朵凑近钟面听齿轮转动的声音,“这钟走的是日子,不是数字。”
去年秋天,祖父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。他常常对着座钟坐一下午,有时会突然问:“你奶奶怎么还不回来做饭?” 我指着钟面上的照片 —— 那是后来洗出来的祖母的照片,就贴在罗马数字 XII 的旁边。祖父看了很久,忽然伸手去摸照片,指尖颤得像秋风里的叶子:“她年轻时,辫子比这钟摆还黑。”
上个月回家,发现座钟的钟摆停了。父亲说游丝彻底断了,找遍全城也没找到会修的人。我蹲在钟前看那静止的指针,忽然发现钟面上的漆皮剥落处,露出底下一层暗红的木头,像是岁月渗出来的血。祖父坐在竹椅上打盹,阳光照在他脸上,把皱纹里的阴影拓印在座钟的玻璃罩上。
“要不扔了吧。” 母亲轻声说,目光掠过座钟底座堆积的灰尘。祖父像是被惊醒的鸟,猛地抬起头:“不能扔。” 他声音很凶,随即又软下来,“等开春了,找个修钟的师傅来。”
我知道不会有修钟的师傅来了。就像我知道,祖父其实早就记不清修钟是为了什么。可他每天还是会坐在座钟对面,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,敲出滴答滴答的节奏。阳光每天准时斜切过八仙桌,把他的影子和座钟的影子叠在一起,像是时光打了个结。
前几天整理旧物,在祖父的抽屉里找到个铁皮盒子。打开时,一股樟木的香味漫出来,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根游丝,每根都用棉线捆着,线头系着小小的纸签,上面写着日期。最新的那根纸签上,字迹已经很潦草了,像是用颤抖的手刻下的密码。
座钟还立在客厅的条案上,钟摆安静地垂着,像根悬而未落的泪。有时起风的夜里,我会听见齿轮转动的轻响,像是有人在时光的褶皱里,慢慢走着,不慌不忙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
转载请注明出处:滴答声里的时光褶皱 https://www.w10.cn/keji/1811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