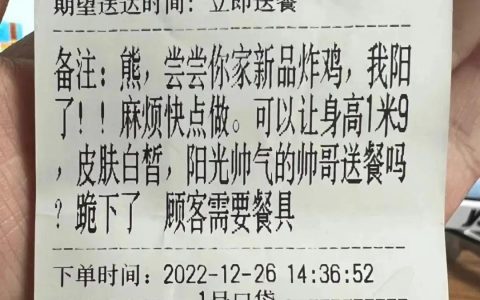青石板路被梅雨浸润得发亮时,巷尾的旧书摊总会准时支起蓝布篷。竹架上码着的书脊像褪色的鱼鳞,风过时哗啦作响,混着隔壁修鞋摊的胶水味,在潮湿的空气里酿成特别的气息。
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摊,是因一本缺了封皮的《城南旧事》。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干枯的紫花地丁,翻开时簌簌落在手心,像接住了某个春天的碎片。摊主是个戴老花镜的老人,正蹲在木箱子前整理书册,蓝布衫的袖口磨出毛边,动作却轻得像在抚摸熟睡的猫。
“姑娘要找哪类?” 他抬头时镜片滑到鼻尖,露出眼睛里的笑意。我举着那本没封面的书晃了晃,他立刻说:“林海音的,去年收的。原主是个中学老师,说书里夹着她学生时代的春游照片。” 果然在扉页夹层摸到硬纸边角,黑白影像里扎羊角辫的姑娘正举着冰棍,背后是早已拆毁的老公园牌坊。
后来每个周末都要绕去书摊转一圈。老人记性极好,会指着某本《唐诗宋词选》说 “这是邮局老张年轻时批注的,他总把‘李煜’写成‘李昱’”,或是拿起《动物庄园》念叨 “前阵子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天天来看,昨天终于攒够钱买走了”。他从不用扫码支付,木盒里的硬币和纸币总被码得整整齐齐,找零时叮当的碰撞声格外清脆。
有次暴雨突至,我帮着把书往帆布下挪。老人从褪色的布袋里掏出两个油纸包,打开时是还温热的糖糕。“这是巷口张婶做的,” 他用袖口擦着眼镜,“她说我总守着摊子不吃饭,硬塞给我的。” 雨珠顺着篷布边缘串成帘子,远处卖花人的三轮车碾过积水,溅起的水花里混着桅子花的甜香。我们蹲在书堆旁分吃糖糕,看雨水在《鲁迅全集》的塑封外凝成小水珠,像给那些泛黄的文字镶了层水晶。
秋末时老人突然多了个帮手,是个扎马尾的小姑娘,总在放学后背着书包来整理书脊。“这是我孙女,” 老人笑着指给我看,“她说要帮我把书都登记到电脑上,说这样别人要找什么书就方便了。” 小姑娘正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书名,遇到生僻字就歪着头问,老人便从怀里摸出磨得发亮的字典,祖孙俩的手指在纸页上轻轻点划,阳光透过篷布的缝隙落在她们肩头,像撒了层碎金。
我在摊上淘到过最珍贵的东西,是本 1983 年的《童话选》。扉页上有褪色的钢笔字:“送给小雅,愿你永远有做梦的勇气。” 夹在书里的还有张游乐园门票,日期是三十年前的儿童节。我把书递给老人时,他翻到某页突然笑了:“这故事我孙女也爱听,上次她还缠着我,让我把书里的狐狸画出来呢。” 他从帆布口袋里摸出支铅笔,在空白处画了只歪歪扭扭的狐狸,尾巴翘得老高,眼睛圆滚滚的像两颗黑葡萄。
冬至那天书摊格外热闹,附近的街坊都来送了些吃的。修鞋摊的师傅拎来袋热乎乎的汤圆,杂货店的老板娘塞了包红糖,连卖糖葫芦的大爷都特意多留了两串不裹糖纸的。老人忙着把书挪开些,腾出地方摆这些吃食,小姑娘则在一旁给大家分一次性碗筷,睫毛上沾着白霜,笑起来脸颊红扑扑的。有人说起这书摊摆了快二十年,见证了半条街的变迁,老人只是摆摆手:“不过是守着些旧时光罢了。” 风卷着雪沫子掠过巷口,书摊的蓝布篷在寒风里微微起伏,像只温暖的船,载着满舱的故事在岁月里慢慢漂。
年后返工的那天,我特意绕去书摊。老人正把新收来的书上架,是几本厚厚的摄影集。“这是前阵子搬家的老陈送的,” 他抽出其中一本翻开,“你看这张照片,是二十年前的巷口,我这书摊那时还只是个小木板呢。” 照片里的青石板路还没铺柏油,穿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经过,车筐里的收音机正放着老歌。我突然注意到照片角落有个模糊的身影,蹲在木板旁整理书册,蓝布衫的背影竟和现在的他重叠在一起。
小姑娘跑过来给我看她的平板电脑:“姐姐你看,我把爷爷的书都做成电子目录啦。” 屏幕上滚动着密密麻麻的书名,每本后面都附着简短的注释,有的写着 “夹着干枯的枫叶”,有的标着 “原主在页边画了小猫”。老人在一旁看着,眼神里既有骄傲又有些茫然,像看着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魔法。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枝,在电子屏幕上投下晃动的光斑,新旧时光就这么在小小的书摊前温柔地交织。
最近去书摊时,发现角落多了个小小的留言本。封面是用旧书皮做的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 “故事交换处”。翻开来看,有人写下找到童年读物的惊喜,有人留下想交换的书名,还有个孩子画了幅书摊的简笔画,蓝布篷下的老人正对着书本微笑。我在空白页写下自己与《城南旧事》的相遇,合上前突然想起第一次来时,落在手心的那片紫花地丁。或许每个来这里的人,都在这些旧书页里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春天。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
转载请注明出处:巷尾书摊 https://www.w10.cn/keji/1748/